“文革”十年后,老友再聚首
1978年2月25日,平反结论终于下达。一个月后,荒煤在女儿的陪同下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
火车在七点多钟停靠站台。走出站口,灯光并不明亮的广场上,张光年、冯牧、李季、刘剑青等人急急地迎上前来,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问候声、笑声响成一团,让荒煤在春寒料峭的夜晚感觉到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暖意。
从张光年的日记看,那天,这已是他们第二次前往车站迎候了。按照列车抵达的时间,一行人六点二十曾准时赶到车站,火车晚点一小时,于是他们回到离车站较近的光年家匆匆用过晚饭再次前往,终于接到了荒煤。很多年后,荒煤都能清楚地想起那个清冷的夜晚,人群熙攘的北京站广场上,那几张久违了的面孔。多年不见,他们虽然都已明显见老,但久经风霜的脸上,却充满着惊喜和掩饰不住的热情。
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张光年先于他人而复出,此时已是《人民文学》主编,并担负着筹备恢复作协、《文艺报》的工作。这位诗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较少提及:“‘文革’初期那几年,我们这些由老干部、老教师、老文化人(科学家、文学家、文艺家等等),组成的‘黑帮’们,日日夜夜过的是什么日子?身受者不堪回忆。年轻人略有所闻。我此刻不愿提起。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吧。”(张光年《向阳日记》引言,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个被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他在十五岁时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他最痛心的是,他的妹妹——一个与周扬从未见过面远在乌鲁木齐的中学教师,却因周扬“黑线”牵连而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他的衰老怕事的老父亲因两次抄家受惊,脑血栓发作而去世……他自己在经历了残酷的斗争后又经历了七年干校时光,风餐露宿、面朝黄土背朝天,学会了在黑夜里喘息,也在黑夜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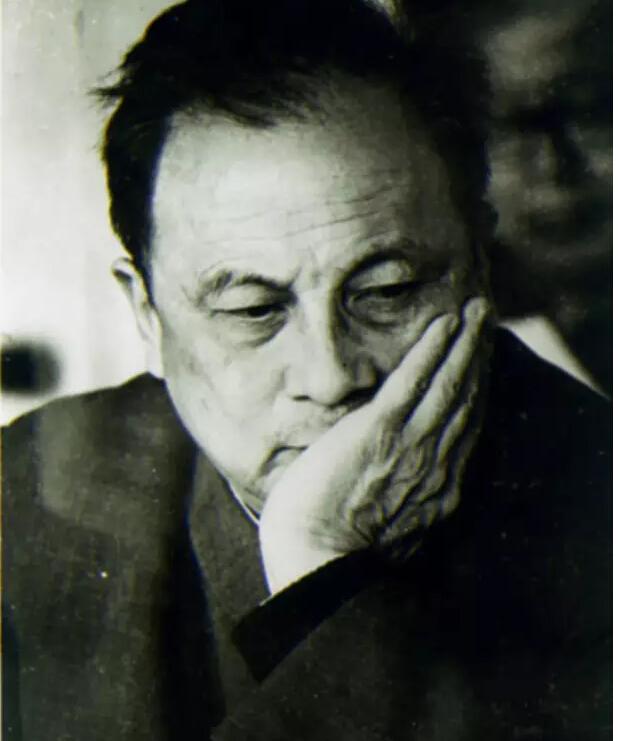
冯牧
1978年那晚的北京站广场,出现在荒煤面前的冯牧面色消瘦,声音却一如既往的干脆洪亮。青年时代起冯牧就饱受肺病折磨,父亲曾担心他活不到三十岁,他却带病逃离沦陷的北平,不仅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还闯过了病魔把守的一道道险关。“文革”时,他和侯金镜等人因暗地诅咒林彪江青被关押,凶狠的造反派竟挥拳专门击打他失去了功能的左肺……他挺过来了。从干校回城看病的日子里,他曾经用篆刻排遣漫长的时光,倾心之作便是一方寄托了许多寓意的“久病延年”,“病”字既代表肉体上的创痛,也暗指那场席卷祖国大地的政治风暴带给人们心灵上无以复加的深切痛苦。当得知周扬从监狱中放出来的消息时,他和郭小川等人立刻赶去看望。为了不被人发现,用的是假名。那天,周扬看见他们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说起在狱中,为了使鲁艺的同志不受牵连,为了防止络绎不绝的“外调者”发起突然袭击,他曾经一个个地努力回忆鲁艺的每一个人,竟然想起了二百多个人的名字……听到这里,冯牧和同去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迎接荒煤的人中,李季的笑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灿烂。几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易激动、性情最豪爽的一个,“文革”的苦难,干校的磨砺,失去最亲密战友的痛苦,并没有让他消沉,他很快就把自己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他的兴致勃勃和精力充沛让刚刚从重庆回到北京的荒煤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
当年站前广场的一幕在张光年的日记中同样描述得十分清晰。尽管此前他已和荒煤通信多次,对荒煤的近况较为了解,连荒煤此次进京的理由——“给《人民文学》修改文章”也是在他的策划下实行的,他还是在日记中写出了自己的印象:看上去荒煤身体很好,或许是因为兴奋,他觉得荒煤好像还显得年轻了。其实,真正使他高兴的是,他知道自己迎来了一个能够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北京需要荒煤,他希望既是文化人又有行政能力的荒煤到作协去。事后看,实际上,此时还有一个人比张光年更加急切地等待着荒煤的到达,那就是沙汀。这位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时期就和荒煤同甘共苦、并担任了荒煤的党小组长的老哥,正打定了主意要把他弄到文学研究所去,而荒煤还全然不知。

荒煤到京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去看望夏衍。次日,去看周扬。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十几年后与周扬的第一次见面:
上午与文殊去周扬同志家,会见全家。灵扬首先建议先调来文研所,周扬则主张兼作协工作。
(荒煤日记,1978年3月12日)
有些让人惊奇的是那天的日记简单平淡,没有劫后重聚的细节描述,更没有荡涤于心的情感流露,那口气倒有点像间隔数日后的一次工作碰头。相比之下,荒煤与夏衍见面的日记虽然同样简洁,但一句“长谈一上午”的背后却似乎蕴含着许许多多说不完的内容——那天,他是提着两瓶酒去的,尽管他明明知道自己和夏衍都不喝酒,但历尽生死后的相见却有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
我曾经问过荒煤,间隔十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周扬是否谈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荒煤说只是一带而过。和周扬一见面就是谈工作,这是周扬这个人的特点,无论什么时候见面就是这样,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说的,他心里装满的都是工作……在这里,周扬“只谈工作,从不谈心”的特点又一次得到验证,不过对“文革”后第一次见面即大谈工作,荒煤到底是赞许还是遗憾却真有些说不清了。
荒煤的话让我再一次注意到周扬对“文革”个人经历的有意忽略。在这一点上他和夏衍是完全一致的。每当有人问起,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话岔开。很显然,那是一段长达十年的黑暗和空白,无论是周扬还是夏衍都不愿更多地提及——那是他们心中的痛,也是他们所忠诚、深爱的党和领袖的疮疤。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渡过了那些黑暗之后,周扬的一只耳朵聋了,夏衍的腿瘸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对党的忠诚依旧没有丝毫改变。周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刚出狱时曾经对儿子周艾若说,感谢毛主席,不然出不来。当儿子反问,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沉默不语。

周扬似乎不喜欢回忆过去,而更渴望面对未来。就在与荒煤见面后不久,美籍华人赵浩生来访,当问及“文革”受迫害的心情时,他说:“一个人不管有怎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受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我在‘文化革命’中所受的种种迫害,我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的贡献更大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话。有些同志对革命贡献很大,他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昨天再沉重也已经走过来了,重要的是如何迎接明天,如何使文艺界这支伤痕累累的队伍重新集结出发,周扬习惯地把这个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1978年9月,以周扬为首,苏灵扬、露菲、张光年、李季、荒煤、冯牧、孔罗荪等“八人三辆小车,9时出发,12时抵任邱(华北油田)总部”,开始了为期四天的考察。张光年是不顾夫人的反对带病而来的;荒煤从繁琐的事务中抽身,带了不少问题来;身着一身工作服的李季好像是回到了当年在玉门油矿深入生活的年代,他忙前忙后马不停蹄,还自称是他们中间身体最好的一个——这种“自夸”在一年之后被打得粉碎。这是一次少有的人员齐备的集体出行,四天的时间给了他们交流、沟通和养息的机会。后来这次出行,被有的研究者称为文艺界重组的酝酿过程之一。那时候,队伍正在起步,经历了大劫难后的他们,在周扬周围迅速汇拢,既为周扬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也成为他复出后拨乱反正的核心力量。
选自《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
《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