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抑制公民议政的国家设计使苏联走向了灭亡
要点1:诚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在统治术上都有高超的发明与发现,都以开国时期的高压政治建构,维持了王朝权力的连续性。但这不是国运昌盛的保证,而是预埋了国运衰微的定时炸弹。
要点2:现代国家稳定的民主政体建构,为议政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由于国家权力并不以暴力机器打压政见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而是保障理性议政的安全性,因此,社会公众不再陷于那种要么服从、要么造反的极端政治境地里,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不至于有丧失自由、失去生命的担忧与危险。
要点3: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初步完成了物质器物层次的现代转变,但现代国家的深层制度建构才刚刚启动。对中国而言,现代建国还显现出前路漫漫的长程性。
要点4: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顽强前行、艰苦努力,可能落定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平台上;疏忽不察、故步自封,则可能被打回贫穷落后的“原形”。为此,大力聚集建构现代国家的宝贵资源,便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建国进程的必需。而其中一项关系重大的事务,就是广开言路、倡导议政,汇聚向心力、展现向上性。
【编者按】“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初步完成了物质器物层次的现代转变,但现代国家的深层制度建构才刚刚启动。对中国而言,现代建国还显现出前路漫漫的长程性。”政治学者任剑涛在其新著《静对喧嚣:任剑涛访谈对话录》中对中国源远流长的议政传统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任剑涛认为现代建国与传统立国的根本差异导致了议政在这两种结构的国家中完全不同的处境。在现代国家中,议政乃是公民职守,是天赋权利、平等的象征;在古代国家,议政是臣民使命、恭顺的标志。在中国的现代建国大业中,必须大力聚集建构现代国家的宝贵资源,广开言路、倡导议政就是其中一项关系重大的事务。因此,复苏中国的清议传统就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
中国古代的议政传统呈现出明显的衰变轨迹
中国古代的议政传统,源远流长。富有传统的议政,一直发挥着矫正中国政治运作偏失的作用。这个传统,有其值得高度肯定的价值。一方面,这使中国历朝历代总不乏志士仁人,匡正时弊、力澄清明、讽议权贵、纯化政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这个传统的走势,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衰变轨迹。从汉代的清议,到魏晋的清谈,最后落到明清的莫谈国事,士人名流的议政力度,愈来愈弱;议政的热情,越来越低;论政的效果,愈见不彰;受制于权力的支配,倒是愈益明显。
中国古代的议政,明显表明:昌盛的国运,在仰赖圣明君主的情况下,不需要士人名流议政;一旦国运衰颓,处士横议,既定秩序出现皲裂,议政导致皇权对秩序安危的极度担忧,因此常常引发镇压党人的政治危机,反倒成为国家倾覆的一个导因。如果历史允许假设,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东汉太学生的议政,不遭遇党锢之祸,也许对缓解外戚和宦官的滥权,有很大帮助,东汉也许不至于迅速陷入衰颓状态,终至国运衰微,朝代更迭;如果魏晋时期,不是因为曹氏与司马氏全无规则的争权夺利,让士人名流只能遁入药和酒的世界,以玄谈空论应对政治压力、保全身家性命,而能够有一个制度回馈的机制,让士人名流在政治舞台上尽情发挥,魏晋之际或许也不会成为一个秩序高度紊乱的时代,而是一个政治清明、思想繁荣的时期;如果明代朱元璋建政,不是以起自社会底层的自卑来建构国家的运作制度,因此竭尽全力打压士人名流的议政热情,以文字狱和八股文一打一拉的手段挤压整个社会,明代或许会出现一个与历史完全不同的盛世景象。
中国古代士人名流的议政高潮,总是出现在政治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此时,往往处士横议、群情激昂,政争激烈、互不相让,官宦对垒、你死我活,完全缺乏理性议政的政治氛围,也缺乏引导士人名流理性议政的制度建设契机,更没有限制国家最高权力实行分权制衡的意念。因此,士人名流议政的热情,大多基于高昂的道德热情。一旦皇权或驾驭皇权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加以镇压,士人名流的议政往往不堪一击,就此被彻底击溃。结果,政治滥权与政治专断相互伴随,造成一幕幕暗无天日的政治悲剧。
专制政治下的治权民主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有限
中国的议政传统,是专制政治的特殊产物。中国古代的专制,当然是从权力归属上加以确认的。政权的不民主与治权的局部民主,是一种不对称的结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一种政权专制的体制。虽然在权力结构上,古代重要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也曾设想过以更高层级的“天”权来限制皇权,但由于没有开出教士身承的教权体系,因此不过是一种德性威慑而已。在皇帝圣明有所保证的情况下,治权的制度性划分,使中国保有局部的分权运作民主特征。但这种被现代部分新儒家所称道的治权民主,其实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极为有限。原因在于,在一个政权不民主的体制中,人们既然相信“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权力逻辑,它也就一定会秉持政治高压统治的理念。东汉的清议,不过是政治高压处境中权力不规范分裂促成的一时的政治“奇迹”而已;魏晋的清谈,则是政治权力明显不规范运作导致的对政治的噤若寒蝉,对风花雪月、哲理玄谈的畸形偏好;到了明清两代,专制政治体制的超高压运行,让一切试图保持政治清明的尝试,只能运行在权争的罅隙之中。诚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在统治术上都有高超的发明与发现,都以开国时期的高压政治建构,维持了王朝权力的连续性。但这不是国运昌盛的保证,而是预埋了国运衰微的定时炸弹。

明末东林党人雕像(图片源于网络)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中,议政作为官权,被纳入体制之内,成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严格说来,这不是身在权力之外的议政,而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一部分。身在权力之外的议政力量,只有汉代太学生和明代东林党人、复社文人,但他们的遭遇,让人扼腕。他们所上演的一幕幕议政大戏,均以悲剧收场。这证明,中国以朝代更迭书写的阶段性历史,呈现出的特证是议政不足,无法消化政治纷争,无法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量,根本实现不了权力分享带来的持续和平的制度建制,最后,只能以朝代政治的崩溃作为代价。一个朝代,即使是国运久长的朝代,也不过是为政治的定期动荡预备,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如果免除这些带给中国人深重灾难的朝代更迭,从周代延续至今,那才是令人赞叹的政治奇迹。可惜,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罢了。
组织化议政生发和保障了美国的生机与活力
在现代国家演进的历史中,呈现出一个引人注意的基本现象:国运健,倡议政;国家衰,禁议政。这自然是一个一般的描述。具体地讲,现代国家的议政,与一个国家处在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还是处在民族国家建构的非规范状态,具有内在关系。诚如前述,现代国家的一般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但实质结构,即政体结构则大为不同。民族国家可以与多种政体搭配,形成诸如君主国体制的民族国家、宪政民主体制的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体制的民族国家等等。只有在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的民族国家中,议政才被提倡,才处在蓬蓬勃勃展现出来的状态,才被视为政治正能量,才有助于国运的昌盛。至于其他两种政体的民族国家,就要看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领袖,其政治态度是开明还是专断。国家首脑个人或政党组织集团的政治取向,对整个国家的议政情形具有决定性影响。

讽刺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艾森豪威尔总统权力被架空的漫画(图片源于网络)
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当然,两国在议政上,都有限制。尤其是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泛滥之际,“恐共症”弥漫全国。其间,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就是对议政的限制,已经成为政治丑闻。但一般来说,美国保护公民议政权利,从法案到一般制度、从国家权力到社会公众、从传播媒介到公民组织,都具有高度共识。尤其是“第四权力”即媒体权力的兴起,让新闻自由主导的社会议政,成为促使国家权力健康运行的强大社会力量。美国人普遍相信,“若不给我新闻出版自由,我就将给这位大臣一个腐败的贵族院……和一个卑躬屈膝的平民院……我就将使他享有那个职位所能授予他的一切权力,去进行威胁利诱——但是,一旦我拥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精心建立的强大体制进攻……把它埋葬在它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正是如此生猛的组织化议政,让国家权力不仅接受法律的约束、权力间的制衡,而且更加小心地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美国的生机与活力,由此得以生发和保障。
抑制公民议政的国家设计使苏联走向了灭亡
反观苏联,国家权力当局自认为占有了真理,以国家权力全方位、高强度地压制社会公众的议政。在抑制公民议政的国家设计上,不仅在国家权力方面搞出一套以特权压制权利的机制,而且在各个方面挤压社会空间:言论、出版自由根本无从提起,公民也很少有就国家发展发表理性意见的空间和媒体;此外,国家开动权力机器,制造个人崇拜,以血腥镇压扑灭不同意见,以极其发达的特务政治严密控制公众的日常生活,国家只借助宣传机器向人们灌输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国家运行在这种窒息生机的体制中,焉能不走向灭亡?
中国的议政传统属于古代,美国和苏联的议政状态发生在现代,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议政。传统议政与现代议政的分野,是现代国家兴起必然引发的后果。在现代议政的机制中,只要免除了极权政治威胁,议政一般不会引发政治风险。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稳定的民主政体建构,为议政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由于国家权力并不以暴力机器打压政见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而是保障理性议政的安全性,因此,社会公众不再陷于那种要么服从、要么造反的极端政治境地里,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不至于有丧失自由、失去生命的担忧与危险。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流,分化的社会公众在组织化社会空间净化了情绪,缓和了不同意见间的紧张,促成那些秉持不同政治意见的公众加强交流,并由此达成政治共识。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国运昌盛。
皇权统治认为任何人的议政都是一种政治威胁
公民议政,不论是公民个人或组织的议政,还是他们借助于公共媒体的议政,只能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才具有健全的理念、制度的保障和政治的功用。这是由国家的结构类型所决定的状态。现代建国与传统立国存在一个重大区别:现代建国是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公共事务,传统立国是自承天命的皇帝、国王的个人使命。正是这一根本差异,导致了议政在这两种结构的国家中完全不同的处境。在现代国家中,议政乃是公民职守,是天赋权利、平等的象征;在古代国家,议政是臣民使命、恭顺的标志。国家结构处在古代状态,或是现代情形,会对议政造成根本不同的影响,而议政的政治后果也大不一样。
在中国,传统立国的排斥性很强。别说土地与生民都属于皇帝,就说立国的绝对精英主义导向,也将平民百姓排除在国家事务的范围之外。一方面,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英明神武的君主。在开国过程中,颇具领袖风范,招纳天下英才,共襄建国大业。立国,不过是皇帝个人建立不朽功勋的专属事务。即便是开国功臣,也不得不臣服于皇权,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皇帝一旦夺取国家权力、黄袍加身,几乎都有大规模斩杀开国功臣之举的原因。这是维持皇权专制和家族特权的必需之举,也是皇权专制的国家政体所必须仰仗的政治集权手段。因为,不斩杀开国功臣,开国帝王尚可威震名臣,力压大臣骄狂,维持皇权秩序;一俟开国皇帝驾崩,二世以下,常常无法镇住开国功臣,既定的皇权秩序,因此受到威胁。故而,即便权力内部的议政,也不见容于皇帝。另一方面,在权力机制的边缘或外部,士人名流基于道德清流的立场议政,在既定的皇权体制中,尽管保有政治忠诚,但对皇权垄断性地聚集统治资源是不利的。只要清流与当道冲突,不管双方如何信誓旦旦忠于皇权,一旦哪方说动皇帝,另一方的言论有害皇权永固,那后者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皇权政治,从根本上不信任任何人的议政,认定那都是一种政治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各个朝代,对议政总是心怀疑惧、慎加提防的深层缘由。这是权力自私的国家本性上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
现代国家以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为核心任务
现代建国,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事务。私权的国家保护与公权的法治规范,两相写照,构成现代国家的结构特点。在现代背景中,国家的建构,不再以皇帝的个人权威、国家的自身权力为基本取向,而以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为核心任务。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催生了工具性国家,告别了目的性国家。至于国家的自身构造,一是需要以高级法限定人定法,二是需要在人定宪法之下建立法治体系,三是需要在分权制衡原则下确立权力建制,四是需要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健全互动。总而言之,对公权的公共特质的捍卫,成为人们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权力导向。促使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公平地获得政治角色、公正地享有公民权利,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现代国家,不再像古代国家,尤其是古代中国那样,极力限制民众的议政冲动。相反,它大力保护公民的议政热情,推动公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倾情关注。
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建构,在政治权力的限定与政治权利的保障上,为政治清议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在国家权力机制的设计上,官方的制度化议政机制扎实地建构起来。议会,就是保证公民参加国家权力决策的重要制度设置。作为国家权力机构,议会制定法律、审查政府预算、监督政府依法运作。作为人民主权基点上的代议制机关——议会,其议员必须反映他所代表的选民意志,进行和平的政治博弈。议政者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一味揣摩皇帝意图,展开残酷的权争,以你死我活作为权争结局。顾准曾经提到,有人将现代议会命名为议会清谈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现代议会是要做出政治决策的,绝不是一个清谈的处所。议会是现代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平台,是公民议政的制度机制。不过,即使议会成为人们议政的制度机制,现代国家的议政也不再限于权力内部分工的制度化议政,公民社会的发达、媒体监督的机制化构成国家权力外部的议政力量来源。
作为主权者的现代国家人民不能对权力掉以轻心
另一方面,民间的议政,更是现代国家建构公共政治文化的必然之选。在一个政治大一统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中,人们很难设想民间议政的有序情形,总会以专制条件下养成的生活习性,想象民主条件下公民基于权利保障的议政状态。他们会认定,民间的议政一定是乱哄哄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支持,也没有利用制度平台表达意见的能力,更没有成熟的政治技巧。因此,他们也会确信,这种议政并不会有什么改进政治现状、提升政治活动水准的价值。殊不知这种专制习性支配的政治想象,完全是受制于专制思维的产物,根本不清楚现代国家、民主条件下议政的价值与作用。在现代立宪民主国家中,民间议政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国家的人民性归属注定了他们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性,看住替他们掌握权力的那些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可能陷入以高尚道德辞藻伪饰权力专横的泥潭。因此,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不能对权力有丝毫的掉以轻心。而议政,正是发挥权力监督作用的重要方式。民间议政之所以是重要的,亦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失重危险随时存在、随时可能出现。权力在国家结构中虽然被严格限制起来,但是其在运作中存在的飞地、缝隙,常常会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权谋私。因此,不管是对权力机构,还是对操权人士,都必须保持十二分的警惕性,不仅要监督他们制定政策时的公共性,也必须监督他们行政执行过程中的公共性。这对保持工具性国家的现代特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同时,在现代国家中,有法律保护和规范的议政,还是有效的政治减压阀。现代国家,规模庞大、人员繁杂、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这就注定国家内部一定存在必须化解的政治张力——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不同的组织与政党,在政治上都会有分歧,在社会中总是有冲突,在文化上必定有差异,在生活上肯定有纷争。因此,源自不同价值立场、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表达不同主张的议政,将促使公众中存在的政治紧张有效地释放出来。这就不至于像古代社会那样,由于政治制度建制简单化的高压取向,造成控制有效时的臣服、控制松动时的骚乱、控制失效时的颠覆。这样的议政,也有利于激发公民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公民的参与能力和自信,从而保证国家稳定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忠诚。
中国的现代国家的深层制度建构才刚刚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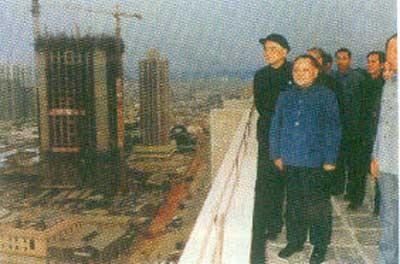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图片源于网络)
当代中国,经由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领域的发展成就,促成两种跟进性状态浮上水面:一是随经济权利而催生的政治权利意识,二是巩固经济发展成就必须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关系到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前者关系到现代财产制度的建构,进而与国家到底是目的性国家以自我维持,还是工具性国家以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的定位发生关联。后者关系到国家是否能够落到分权制衡的法治平台上的大问题。分权制衡,不仅需要在国家总体结构上促成国家权力、社会自治和市场自主的分流结构,还需要民主政体的有效建构以及相关体制的顺畅运转。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初步完成了物质器物层次的现代转变,但现代国家的深层制度建构才刚刚启动。对中国而言,现代建国还显现出前路漫漫的长程性。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顽强前行、艰苦努力,可能落定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平台上;疏忽不察、故步自封,则可能被打回贫穷落后的“原形”。为此,大力聚集建构现代国家的宝贵资源,便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建国进程的必需。而其中一项关系重大的事务,就是广开言路、倡导议政,汇聚向心力、展现向上性。
清议传统的复苏是现代建国大业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建构现代民主中国,是极具挑战性的现代建国大业,远非一人之力、一个组织所能为。动员全体公民积极参与现代建国大业,为之献计献策,是中国迈过现代建国的十字路口,晋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以现代议政机制为平台,激活中国的议政传统,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有效聚集智力资源。基于这样的需要,清议传统的复苏,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复苏的清议传统,不再是纯化皇权政治的手段,也不再是清流、邪党政争的手段,更不是相关人物谋求权力的途径。复苏的清议传统,是现代国家权力建制的制度建构,是公民发挥国家主人作用的有力途径,是社会约束国家的有效方式。在中国既定的代议政治中,源于权力的议政是国家权力制定法律规章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分流的现代架构中,公民议政是监督国家权力、谋求有效自治的基本方式。国家权力,即使没有落定在现代政治的平台上,但因为在国家基本法中已经明确肯定了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公众的议政。诚然,中国还缺乏议政的社会依托,不管这类依托是指法律供给、公民组织,还是公共媒体。但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议政的权利,不容侵犯。而公民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对国家政事的评议,乃是行使公民权利。只要“人民”共和国充分体现它的平民性,以及呈现“共和”的国家政治特性,议政就会具有不可遏制的强大动力和现实需求。
议政传统的复苏,不再重复从清议到清谈再到莫谈国事的衰变轨迹。制度的议政建制,不再为清与不清的利益纠葛而疑虑。因为,现代国家并不需要议政的权力体系中人,秉持一种绝无谋权谋利动机的高尚道德感。国家权力体制内的议政,就是代议人士合法表达其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诉求,在不同表达间形成共识,使不同利益诉求退让式地得到满足。但一切基于以权谋私意图的议政,绝对不为公众所接受,也会被权力惩戒机制所惩罚。而社会公众的议政,乃是基于自由权利得到法权保护基础上的政治评议,无须壮怀激烈,无论动机高低,不计利害得失,最后一定只能落在公共利益层面进行检验。这个时候,中国传统议政刻意区分的清流浊流,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公民议政的时候,不至于让那些抢占了道德高地的人自命清流,而将论争对手打入浊流队伍,反之亦然。不过,议政仍然是有道德规则的,但那是公共德性规则,而不是清浊的道德动机区分。只要公民议政有利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这个公共目的,它就具有了势不可挡的公共力量,并且具有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编辑:陈菲)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法: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主要著作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重思胡适》(主编,2015)等。
图书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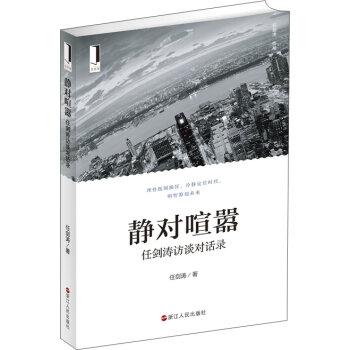
《静对喧嚣:任剑涛访谈对话录》是作者多年来与报纸杂志编辑记者和同道朋友的访谈对话辑录。作者自谓“这类议论,无关国家政策制定、不涉个人升迁,仅仅是一个公民、一个教书匠关切国家前途的书斋议论”。全书充满思辨的魅力、激情的光芒和实践的智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富有深刻的启迪。




